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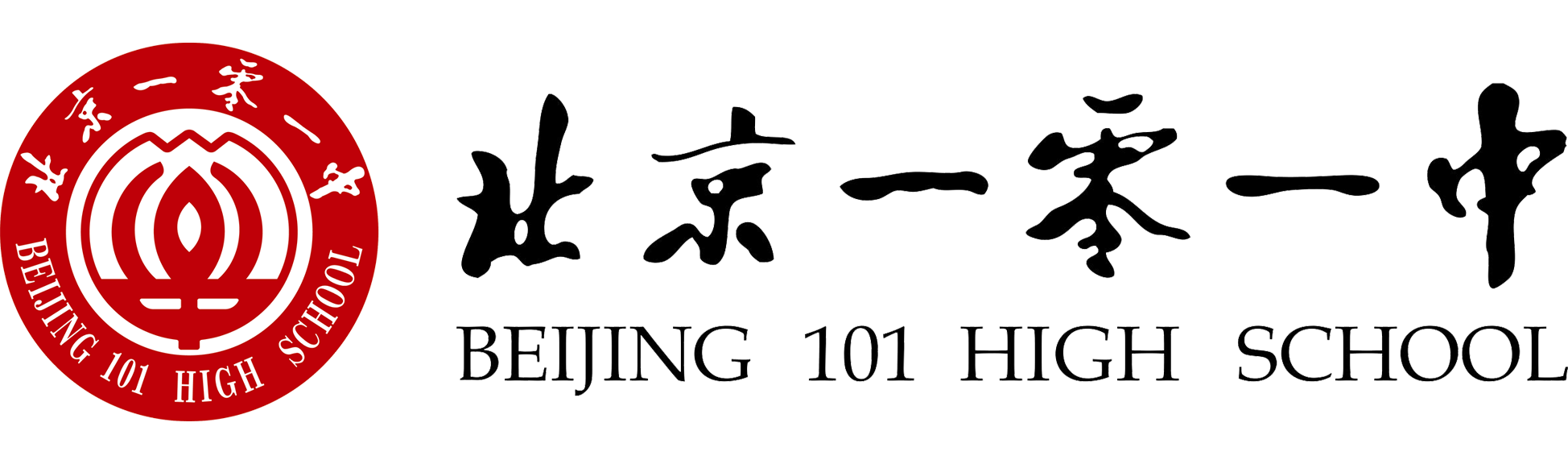
——一零一本部
返回集团导航页
首页党群工作离退休
我是1947年由冀察中学转入边区联中的。我一个人背着被褥和书包从易县大良岗村,一路派饭住宿,走了二百多里地,来到位于滹沱河畔的西黄泥村——晋察冀边区联中所在地。我当时只有十三岁,报到的时候王秘书(相当于教导主任)看我年纪小,便把我编入九班。九班同学的年纪同我差不多,都只有十三四岁,所以在学校被称为“小九班”。
边区联中是准备全国解放后同国统区中学接轨的正规中学。教授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动植物、英语、音乐和体育等课程,国统区中学所有的课程几乎都有。
我们用的数学教材也是范式代数,先学小代数,后学大代数。国文课文除边区作家丁玲、艾青、赵树理、孔厥等人的作品外,还有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张天翼和陈白尘等作家的作品。当然都是作品的片段,但老师讲课的时候往往介绍他们的生平和创作。老师还介绍外国作家的作品,不仅给我们讲过《死魂灵》,还讲过果戈理写《狄康卡近乡夜话》时如何让母亲为他搜集乌克兰农村姑娘服饰的名称。国文老师还给我们讲语法,什么是主语、谓语、宾语和状语,并让我们用图表画出句子的成分。还讲体裁、人称、标点符号,比如什么是报告文学、什么是散文。我们还学古文、,古典诗词。英文每周四节,课文是英文老师自己编的,,现在只觉得英文课很有意思,但都学了什么课文已经完全忘了。
学校有个文工团,由各班学生组成,我们九班有三个同学。平时仍在各班学习,演出节目的时候才集中到一起。也到外地演出过,但时间不长,次数也不多,主要在学校演出,是我们重要的文娱活动。
我们的图书馆的书不多,但五花八门,有延安用马兰纸印的《死魂灵》、《鲁迅小说集》、《表》,还有北京等地出版的老舍的《赵子曰》、《老张的哲学》等书,以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言情小说。《赵子曰》和《老张的哲学》我就是那时读的,情节至今不忘。图书馆不断增添新书,如1947年进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同学们争相阅读,在九班就转了十几天。
郝人初校长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团结友爱的精神。我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,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,也比和平年代的中学生容易培养集体主义精神。没有集体,个人就无法存在。现在提倡的、,宣传的,我们那时已经做到了。
夜行军的滋味很不好受,一边走一边睡觉。不是军训,而是敌人在后面追着,非走不可。我们帮助女同学背东西。我就替她们背过书包,还有人替她们背过背包,绝无想当英雄或向英雄学习的想法。想的很简单,不能让一个同学掉队,因为掉队就可能没命了。
我们分住在村里老乡家,住得很散,一组(五六个同学)睡在一条炕上。晚上在煤油灯下上自习。没灯油了,没墨水了,由组长去领。墨水是用紫颜料泡的,干了后闪金光。冬天当然不暖和,老乡们烧炕,我们没有柴火烧炕,但也快活地过来了。我说快活,因为那时年纪小,并没有觉得生活多艰难。初到西黄泥的时候,九班教室是一间较大的土房。老乡们用泥土给我们制作了“课桌”,一个个用泥土砌的“课桌”占满“教室”,上面还挖了个圆洞,圆洞上立着用半个鸡蛋壳做的墨水瓶。马扎放在桌子后面,使用起来并不比现在中学课桌差。我上面说的几门课就是在这间教室里听的。李后主的《浪淘沙》是在煤油灯下背会的。
九班有学生会,设主席、生活委员和学习委员。没有公开的党支部,因为那时党员尚未公开身份。九班有过两任班主任,白先生和江先生。白先生来自延安鲁艺,是老作家李又然的学生,所以给我们讲过她老师的散文《吉普车》。白先生像妈妈,对我们呵护备至。一天,白先生上课精神不大好。下课后女同学告诉我们,她们屋里一位女同学被蝎子蜇了,白先生听到马上赶来,把她背到卫生所上药,折腾了一夜。
江先生比白先生小,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,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。他来自北京的某所大学。他同我们打成一片,像大哥哥。他好像不大管生活上的事,更关心我们的学习。比如学英语的时候,教我们如何记单词,如何最大限度使用自己的记忆力。学几何的时候,告诉我们解题一定要从“己知”出发,运用逻辑推理演算。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不少学习方法。
我写的是战争年代我们如何生活和学习的。这段峥嵘岁月像一首歌,至今仍在我的心中回荡。
(作者蓝英年系著名学者、翻译家,边区联中1949届毕业生,著有随笔集《青山遮不住》、《蓝英年随笔》,译著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等)

1947年联中文工团劳军出发前